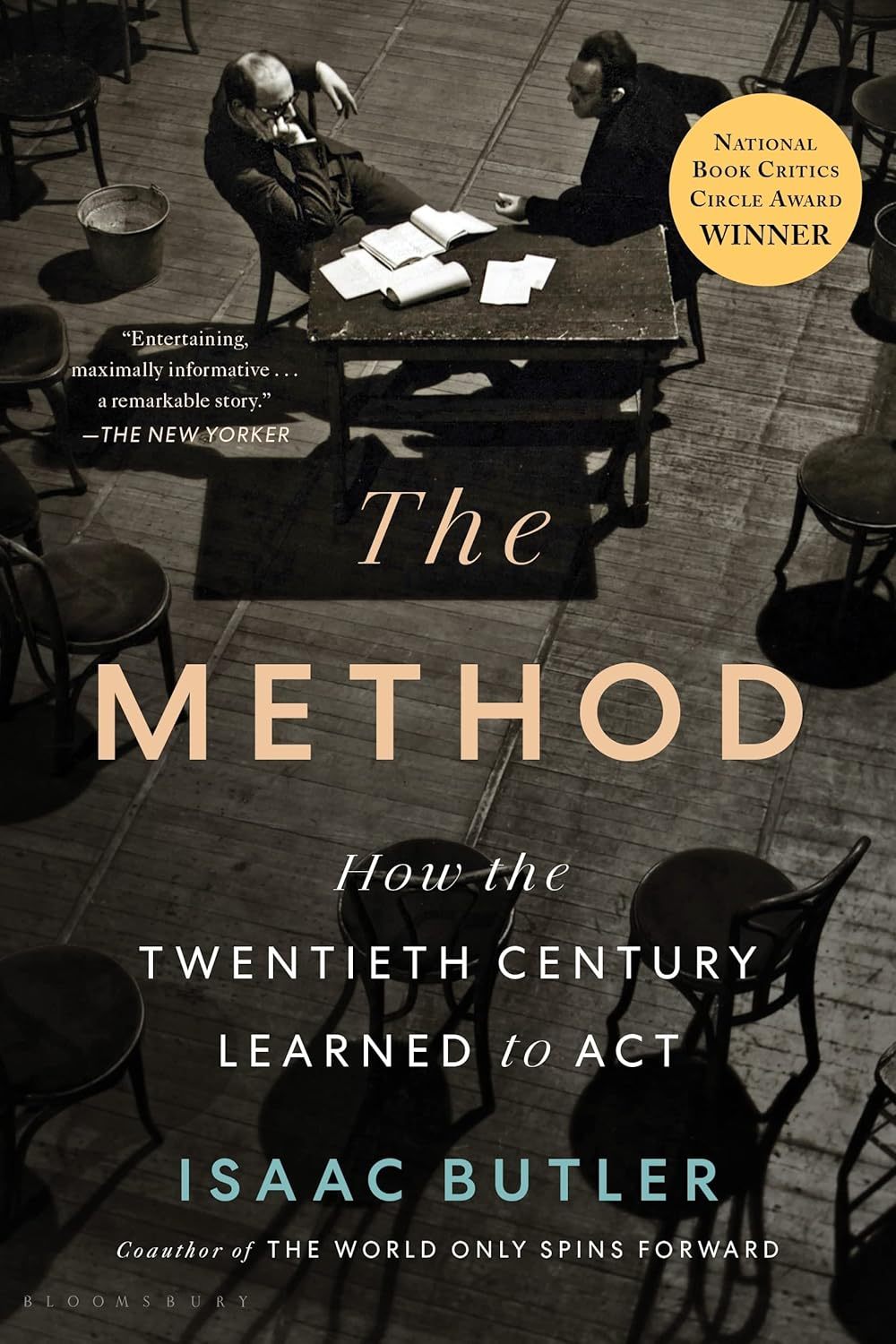
Issac Butler, The Method: How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rned to Act, Bloomsbury, 2022
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到美式表演“方法”
作为一名伟大的演员、导演、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终其毕生精力,探索演员如何塑造人物和创造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部著作中题为“How an Actor Prepares”的一部被翻译为“演员的自我修养”,也让“自我修养”这一表达成为长盛不衰的流行语。表演工作的核心,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在于将意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尽可能贴近角色的心理和人物的内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操控演员的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转向强调表演中身体动作的训练。第一阶段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训练演员理解角色的行为动机,第二阶段则侧重表演所需的具体身体技术。表演工作高度依赖演员的身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旨在帮助演员把角色的内在状态通过肢体以外化,为特定角色探索一套行为表现方式,从而实现演员用自己的身体活动体现角色的心理活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俄国传入美国以后,启发一大批戏剧表演艺术家前仆后继地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执掌演员工作室(The Actors Studio)的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继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方法派”表演风格。从声名远扬的团体剧院(The Group)和演员工作室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演员训练专家,他们与斯特拉斯伯格求同存异,基于个体阐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展开了多样化、创造性的实践。身兼演员和表演学者双重身份的埃塞克·巴特勒(Issac Butler),在其所著《方法:二十世纪的表演课》(The Method: How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arned to Act,后简称《方法》)一书中,雄心勃勃地呈现了表演风格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叙述与分析围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建立、演化、传播以及美国式方法派表演风格的嬗变展开。
在现代主义颠覆了自启蒙运动以降的文学和艺术传统这一背景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联同无调性音乐、现代主义建筑、抽象派绘画等——改变了人们的艺术欣赏和美学品味,人们开始重视自我与他者、周遭世界在持续互动中生成的经验和主体在情感体验、反思性基础上形成的内在世界。《方法》一书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掀起的表演风格革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巴特勒的历史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实际上看到不止一种“体系”或者“方法”,而是艺术家们针对什么是好的表演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鸣。
体验、动机与心理技术
故事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科钦创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俄国社会将演员看作是地位低贱的群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出生于家境优渥的富商阶层,从小就对戏剧和表演感兴趣,成长中经常在剧团与演员打交道。在执掌莫斯科艺术剧院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做的许多工作是为了提升演员的社会地位,他给演员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准则,认为演员要想被当作艺术家对待,他们首先需要遵守工作的纪律和职业的伦理。并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通过开发一系列的表演训练,试图提升演员表演的技能水平。总之,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训练和管理演员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希望通过提升演员的专业化程度,让社会大众尊重这一职业,起到了推动演员的职业化进程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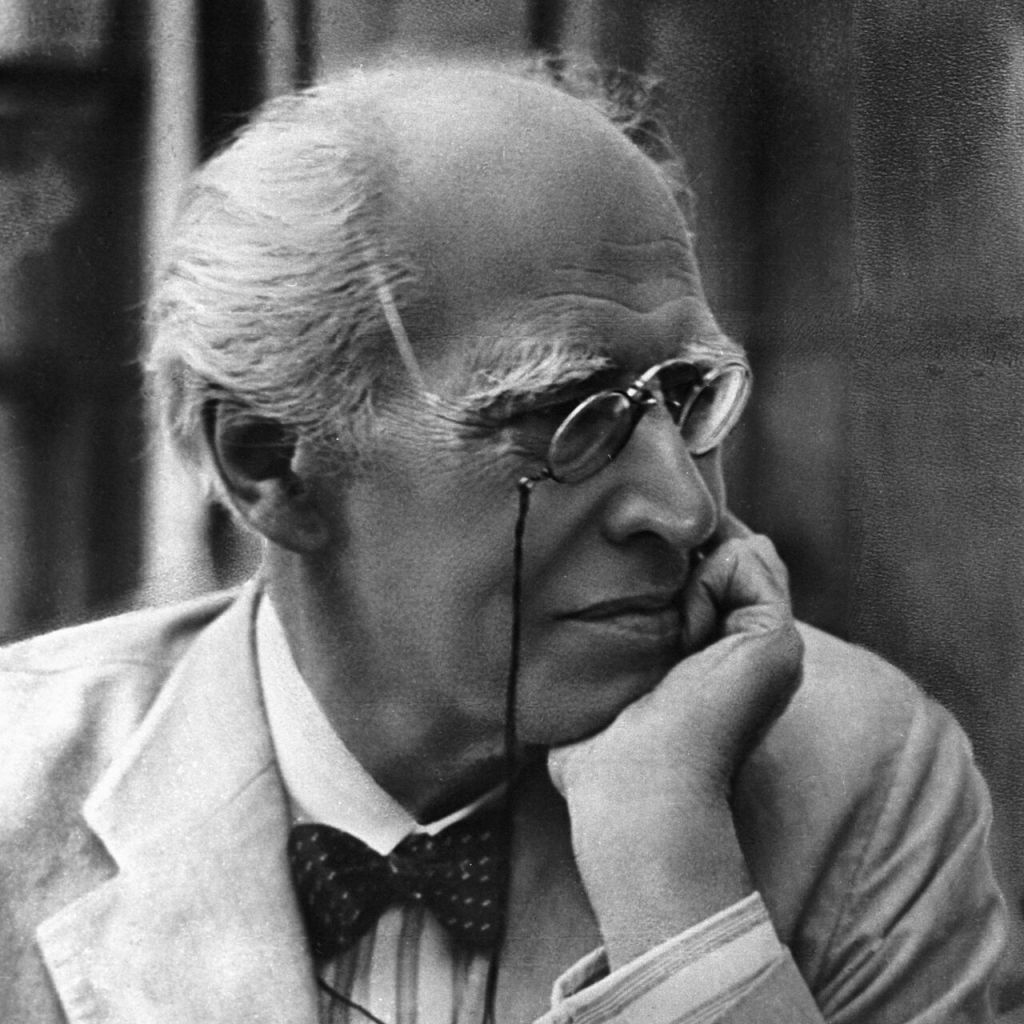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表演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演员在舞台上演绎的并非标签化的人物类型,而是由独特的生命经验和具体的情绪感受定义的鲜活的个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抽象的观念层面,标志着表演风格从强调外在表征到内在真实、从以象征到经验为核心的转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承认演员自身在表演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首先,演员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个体经历会塑造其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其次,表演的过程是演员的自我遭遇角色的自我的过程,两者在剧本的规定情境中有机互动,最终演员在表演的现实与观众的想象空间中与其表演的角色融为一体。
演员成为角色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许多时候演员甚至无法在心理上接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有的人物做出的行为不符合演员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有的角色生活的年代迥异于演员生活的当下,等等。通常演员在表演的准备环节,会进行深入的剧本剖析,将故事情节和角色化整为零,通过拆解构成角色的元素和特质,找到演员可以与角色产生共鸣从而相对容易掌握的,以及演员觉得缺乏共鸣从而较难把握的部分。对角色感同身受是一种高阶状态,意味着演员需要在主观层面体会角色说话、行动的内在动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强调“动机”这一概念,认为演员需要理解其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处境中做出特定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角色如何被其内在所驱使从而做出行动并产生后果。如今“行为动机”一词对表演从业者、观众群体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代,认识到演员必须对角色的行为动机达到同情共理甚至是感同身受,从而才能准确地扮演角色,这对表演艺术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甚了解,他在指导表演和训练演员的过程中强调演员有意识操纵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内心活动,以帮助他们在角色的思想和情绪感受中游走自如,这依赖的是“情感记忆”(affective memory)。情感记忆是一种颇具争议的表演技法,通过唤起演员的感官记忆,撬动演员的情绪感受,来激发演员与角色产生共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了各种帮助演员深刻把握角色内心世界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心理技术”——一套将演员自我融入角色的练习。它的前提在于认识到演员的意识、情绪和感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被自我操控而时刻处于变化中的。当故事中的人物做出特定行为时,演员通过调动自己的生命经验来体会角色行为的内在动机,有意识地操纵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将来自内心世界的情绪感受投射到角色上。心理技术训练演员敏锐观察与深入体会日常生活的种种,通过追忆的方法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情绪感受与所塑造角色的行为举动和内心世界有机联系起来。当演员可以自如地操控自己的意识并调动生活经验和情绪感受——也就是在心理技术上训练有素时——便可以尽情地在表演中经历角色所经历的生活和体验角色所体验的情感,从而将演员的自我移植到角色的世界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导演员不要在舞台上机械地展现故事和人物,而平时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学会调动自身的经验和情绪感受来把握角色。
表演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之感,源自演员将自己设身处地置于角色所处的时空、境况之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另一核心概念是“规定情境”(given circumstance),可以理解成角色所处的特定生活环境及其身处的境遇。所谓的规定情境虽是角色世界里的,但演员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也很有可能身处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训练演员将角色的规定情境拉回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虚拟和现实的相互映照中,演员思考如何适应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打磨表演细节。演员根据角色的规定情境阐释角色行为的内在动机,是表演迈向真实性的努力。
表演中的真实性被巴特勒定义为“心理和情感层面的真相”(13页)。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终极的真实并不可能。即便演员尽可能在角色的规定情境中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但无法对角色的内在状态和心理活动进行精准复制。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表演的理想状态可以用“好像”(as if)一词来刻画。人类表演学者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好像”说明人类现实的多重层面,当我们细致完整地深入每一层面,其中的“好像”把行动从前因后果中剥离出来。好的表演能够带给观众一种“好像”的感受,他们一方面接受了戏剧超越日常生活的虚构性,另一方面也捕捉到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人物行为等并与之产生共鸣([美]理查德·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系列:谢克纳专辑》,孙惠柱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演员为了让表演达到“好像”的状态,需要深入体验角色。“体验”(experiencing)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核心要义,俄语中“perezhivanie”一词有经历、体验或者重新经历、重新体验的含义,曾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直白地翻译成“活出角色”(living the part,85页)。当演员进入所扮演角色的世界,在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中想其所想、感其所感、想象其所想象,他/她朝着活成角色的样子而努力。演员成为角色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而自我的意识、情绪感受等都被演员积极地掌控和调动,以达到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体验角色的目的。这样一来,表演过程中演员的自我也被角色重新塑造了,当演员“好像”成为了角色时,观众会强烈地感受到表演的真实性。不同于纯粹技术(包括声音、肢体)的展示,“体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定义了表演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关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相比第一阶段的心理技术和情感记忆,更强调身体训练。演员通过开发自己的声音条件和肢体动作,在身体中储存对角色的内在动机、情绪感受进行体验而逐渐形成的“肌肉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表演工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带来的深刻变革在于,曾经被认为是属于演员与生俱来的“天赋”,实际上是演员身上可以被系统训练和开发的能力和潜力。换句话说,演员的情绪感受、想象力等等并不是已经成型的特质,演员的内心世界(inner life)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被导演不断挖掘、激发从而产生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表演工作孕育着丰富的创造性。
情感记忆训练法的争议
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传播启发,美国出现了一批继承与发展体系的表演艺术家和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巴特勒呈现的美国戏剧表演的变革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围绕着“方法”(Method)这一关键词,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表演的规范、风格和技巧。犹太裔演员、导演和表演教师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与美国团体剧院的元老哈罗德·克鲁曼(Harold Clurman),并没有全盘照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是将其中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落实到具体的表演技巧(technique)上,在实践中加以调整,以适应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戏剧行业现状和演员个人特质。
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强调在训练演员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其个人的“情感记忆”,由此发展出情感记忆训练法。斯特拉斯伯格认为,如果演员不会调动个人的情感记忆,表演工作不外乎机械重复手势、声调、动作,演员也就无法演绎出人物在特定处境下做出特定行为时的情绪感受——这是角色行为的内在动机和意义来源。假设演员经历过类似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斯特拉斯伯格针对表演技艺的训练着重体现在唤起演员彼时彼刻的情绪感受。当演员打开情感记忆的阀门,涌现出来的也包括个人过往经历中的创伤。除了平时训练中采用,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记忆练习法也贯穿于演员在舞台上或者镜头前进行正式表演的全程,这样一场戏下来,演员通过不断地唤起情感记忆甚至创伤记忆来体验角色,这对演员心理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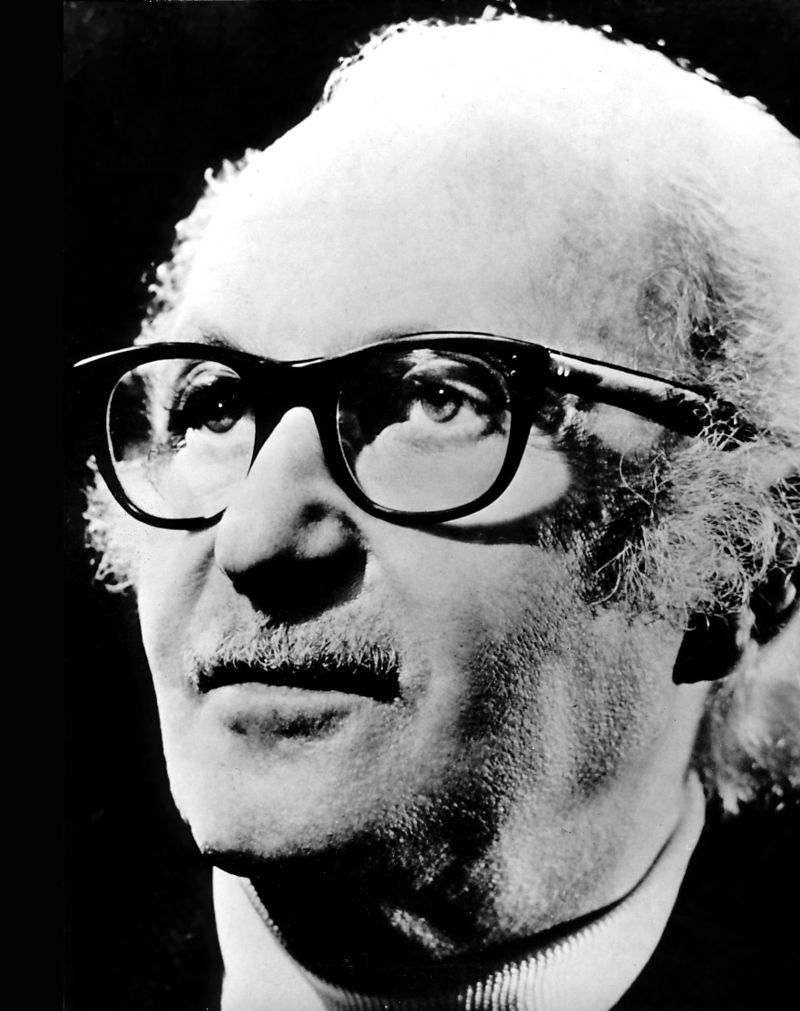
李·斯特拉斯伯格
团体剧院内部就情感记忆练习是否应该被当作表演技艺训练的必要方法产生了分歧。斯特拉斯伯格为了巩固自己在团体剧院和戏剧行业中的地位,大力鼓吹情感记忆练习法,并将其用来培养年轻演员。团体剧院里的另一位表演大师斯特拉·阿德勒(Stella Adler)曾拜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一故事流传下来许多版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阿德勒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剧本赋予角色规定的处境和需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解决的问题,人物受内在动机驱使做出指向特定目标对象的特定行为,规定情境的变化带来角色内在动机和外在行为的变化,不同角色在各自不断变化的规定处境中形成各自的行为链条,人物之间发生相互联结和产生冲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传授阿德勒想象在表演中的重要性,演员通过发挥想象进入角色的规定情境中,理解角色的动机和行为如何被规定情境所塑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通过调动想象力来体验角色的行为动机和情绪感受,他本人并不赞同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记忆练习法。阿德勒也认为团体剧院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把握并不到位,体系的核心实则由三个基本元素及其互动关系构成:剧本给角色规定的情境、角色面临的问题或者待解决的任务、角色的行为与结果。演员通过发挥想象,将这三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厘清,调动情感和唤起记忆是结果,而如果像斯特拉斯伯格那样将针对情感记忆的训练摆在首位,就本末倒置了。
需要澄清的是,阿德勒并不否认演员在表演中体会角色情感的必要性,她反对的只是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记忆练习,也就是将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当成是通过唤起记忆(时常是创伤记忆)来触发情感的结果。那么,记忆到底在表演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交流中,阿德勒倾向于认为表演过程调动的并非是演员的情感记忆,而是感官记忆——这也是她与斯特拉斯伯格的分歧所在。例如,剧中人物拿起咖啡杯喝咖啡,即便舞台上的咖啡杯是空道具,演员在表演这个动作时应该回忆起日常生活中这个动作产生的感官体验(比如刚煮好的咖啡会让杯子烫手)。在阿德勒看来,日常生活中特定行为动作产生的感官体验会留下记忆,被演员放入自己的记忆库存中。如果表演喝咖啡这一动作被演员解码为调动日常生活中喝咖啡带来的感官体验,那么角色的情绪感受该如何通过调动演员的记忆来演绎呢?阿德勒认为情感本身也可以被转化为感官体验,这看起来是从具身化的视角思考表演中情感的表达。

斯特拉·阿德勒
阿德勒认为演员之所以能体会到角色在特定处境中的情绪感受,是回忆起了自己经历类似情境时同样的情绪感受所引发的感官体验,反对演员遵照斯特拉斯伯格那些机械、僵硬、重复性的情感记忆练习。实际上,我们很难判断团体剧院里的哪一位大师继承的是正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因为体系本身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强调角色的内心世界以及演员情感和情动的记忆;第二阶段强调表演中的身体动作训练以及角色的行为和规定情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第一到第二阶段的转变也与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对心理学的忽视自始至终都存在,第二阶段的体系与苏联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并不矛盾,这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保护自己执掌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免于意识形态风险。美国团体剧院内部围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分歧或许在于,斯特拉斯伯格继承的是体系的第一阶段,而当阿德勒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那里学习的时候,体系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了:强调演员在日常生活中,用身体记忆储存行为动作和情绪感受触发的丰富的感官体验,在表演时调动的是感官体验的记忆而非情感记忆。
好莱坞的“方法”革命
让我们暂时搁置团体剧院内部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理解与实践、继承与发展上的分歧,巴特勒提到让方法派表演进入公众视野的第一部作品是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欲望号街车》,饰演男主角的演员马龙·白兰度是第一位家喻户晓的方法派演员。白兰度在历经坎坷的人生中很早就被识别表演的天赋,来到纽约后跟随团体剧院的艺术家学习表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刻画白兰度,可以说他是一位出了名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演员,在片场的情绪爆发经常让剧组不知所措。据说白兰度常常脱离剧本展开即兴表演,为了激发饰演对手戏演员的情绪感受,白兰度在片场不乏出格的行为。白兰度实际上并不完全认可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而认为自己的表演风格主要是受阿德勒的指导和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更接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白兰度通过一部部耳熟能详的作品,成为了美国式方法派表演的代表人物。

《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右)
除了强调表演技术上的准确性,方法派表演风格宣扬一种符合人物内在真实性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为了让自己的表演符合角色真实的内心世界,演员需要调动个人经历中的情感记忆甚至是心理创伤。方法派起初在戏剧和电影业的交集处得到发展,后来因声名大噪的演员玛丽莲·梦露而更多地与好莱坞挂钩。梦露生前与斯特拉斯伯格一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她长期受到心理疾病的折磨,斯特拉斯伯格一直鼓励她接受心理治疗,并配合其对梦露的表演训练。当时的表演行业似乎认为,如果像梦露这样的“花瓶”都能够被训练演技,那么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在好莱坞就大有可为了。梦露的人生悲剧折射了方法如何成为双刃剑,一方面为好莱坞票房做出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对演员本人可能意味着毁灭性打击。因其强烈的心理分析意味,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一方面呼应了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疗愈的自我”(therapeutic self)的流行话语,但另一方面也被批判为一种似是而非、业余甚至有害的心理学。

玛丽莲·梦露
好莱坞的风生水起推动方法派成为美式表演的主流风格。《毕业生》《教父》等电影的主创几乎都与斯特拉斯伯格及其担任艺术指导的演员工作室有密切来往或者师承关系。《毕业生》这部电影反映美国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以及身处其中的年轻人面对进步主义话语时的不安、挣扎与蠢蠢欲动,影片导演并没有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帅哥”来出演男主角本杰明,而偏偏相中相貌平平的犹太裔演员达斯汀·霍夫曼,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本杰明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这部戏从导演到演员都深受斯特拉斯伯格方法的影响,导演在开拍之前深入了解霍夫曼的人生,包括青少年时期第一次失败的性经历。在拍摄本杰明与罗宾逊夫人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的戏时,导演有意识地唤起霍夫曼这段记忆,以激发他演绎角色在规定情境中与曾经的自己类似的情绪感受。

《毕业生》里的达斯汀·霍夫曼(右)
扮演第二代教父的阿尔·帕西诺是斯特拉斯伯格的得意门生。有趣的是,帕西诺本人透露其在表演工作中并不使用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记忆训练,而倾向于调动自己作为演员的直觉。通过对剧本的深入分析,帕西诺洞察角色的特质并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在镜头内外好像都活成了角色的样子,例如举手投足之间总看起来像教父。斯特拉斯伯格反对演员一直背负着角色的包袱或者说承载着角色的身份,认为演员在潜意识里让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在戏里戏外成为角色并不是正确地理解和践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方法派的巅峰时刻莫过于斯特拉斯伯格受邀出演《教父II》中的黑帮大佬海门·罗斯,亲身体验自己传授给一众门徒的方法,切身体会演员使用情感记忆练习面临的挑战:自我的内心世界被角色的心理所占据,角色的影响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

《教父II》里的阿尔·帕西诺
《教父》系列也捧红了新一代演员——手捧两座奥斯卡小金人的影帝——罗伯特·德尼罗。德尼罗塑造过的所有角色中,最著名的当属年轻的教父唐·科莱昂和《愤怒的公牛》中的拳击手杰克·拉莫塔。德尼罗为拍摄《愤怒的公牛》,曾展开长达一年的准备工作,包括与人物原型——拳击手拉莫塔——一起生活,并从他那里学习拳击,辅以对拉莫塔家人的深入访谈。德尼罗为了在大荧幕上看起来更像人物原型,通过运动和饮食增肌十五磅,快速的增重过程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了高血脂等健康问题。剧组对德尼罗的评价是无时无刻不深度沉浸在角色中,为此大家不叫他本名,而叫他在影片中的角色名字“杰克”或者“Champ”(冠军)。虽然《愤怒的公牛》起初在票房和评论口碑上都不尽如人意,但最终为德尼罗收获了第二座奥斯卡小金人。

《愤怒的公牛》里的罗伯特·德尼罗
德尼罗的作品在美国公众当中普及了方法派表演,大众通过媒体报道而熟悉他为表演所做的长期准备工作——包括身体训练所需的高强度投入、对人物原型的生命史访谈、对日常生活的近距离观察和亲身体验——都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接近角色,以在表演中达到自然状态下的真实性。需要注意的是,德尼罗的工作已经偏离了斯特拉斯伯格的情感记忆练习法,面对德尼罗改变自己的身体以在视觉上逼近人物原型,斯特拉斯伯格对此不置可否。然而,斯特拉斯伯格的离世开启了美式表演风格发展的新篇章,无论是“体系”还是“方法”,从此都不可能一家独大了。
优秀的演员为了实现在镜头面前、舞台之上成为角色,即便在镜头之外和舞台之下,也时刻为活成角色而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对身体进行训练和采用情感记忆练习。《方法》一书提及一段值得玩味的历史,它凸显了“体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的关键词——和“表演”之间的张力:在《霹雳钻》(Marathon Man)的片场,霍夫曼向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透露,为了更精准地演绎角色流露的疲惫不堪,他在开拍前几天几夜不睡觉去跑步,以让自己看起来更逼近角色的状态。奥利弗回应道,“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表演呢?”如果说英式表演传统强调训练演员细致把握剧本的节奏和声道,以及控制肢体动作和声音以将文本通过感官体验外化;美式表演传统则强调演员充分发挥自我的潜力,操控内心状态与心理活动,来体验角色的行为动机和情绪感受。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表演传统并非是泾渭分明的,例如美国茱莉亚学院的表演项目就结合了英式和美式的表演传统,既训练演员在表演中说话与行动的技巧,也挖掘演员个人经历、生活经验与内在世界,以达到由内而外打磨演员表演技艺的目的。
总体来说,《方法》通过展示一个世纪里欧美表演艺术家的思想争鸣和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好的表演并不遵循统一的标准。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斯特拉斯伯格的方法,还是由美国团体剧院与演员工作室传播与影响到好莱坞的表演技艺,都强调对剧本的深入剖析与对角色的深刻理解,以回答剧中的人物想要实现什么任务、有何阻碍、如何达到目标等问题。表演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时代持续至今:“角色为何在规定情境中做出特定行为,背后有何动机?”人物内在动机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了陈词滥调,以至于曾有人面对演员对动机的发问讽刺地回应道:“你的工作!”
成为演员与成为人类学家
在《方法》一书的结尾,巴特勒提到目前针对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体验的研究较常采用心理学进路,比如通过在演员群体中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感受和体验角色内心世界的数据。现有数据主要来自欧美社会,一些调查结果发现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反应更多地来自与饰演对手戏的演员之间的互动。目前比较缺乏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表演过程中演员自身体验展开的研究。
前文所述方法派演员的表演准备工作其实很像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通过与人物原型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人类学所说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半结构深度访谈和口述史访谈,演员试图达到走进/近角色的生活世界、理解角色的价值观念与特定处境下的行为动机等目的。经历了“身体转向”的人类学(Xinyan PENG, “You’ve Got to Have Core Muscles”: Cultivating Hardworking Bodies among White-Collar Women in Urban China[J], Ethnography, 2020, 24[1]: 3-22),越来越强调民族志工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把自己作为方法、将身体作为工具,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实现对他者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其生活世界的同情之理解。类似地,演员在表演中通过调动自己的情感、感官记忆,经历角色的生活并体验其内心世界。但演员与人类学者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going native”(成为土著)并不是人类学者的终极目标,而成为角色可能是演员和观众希望好的表演能够最终达到的境界。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彭馨妍评《二十世纪的表演课》|演员如何成为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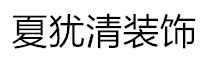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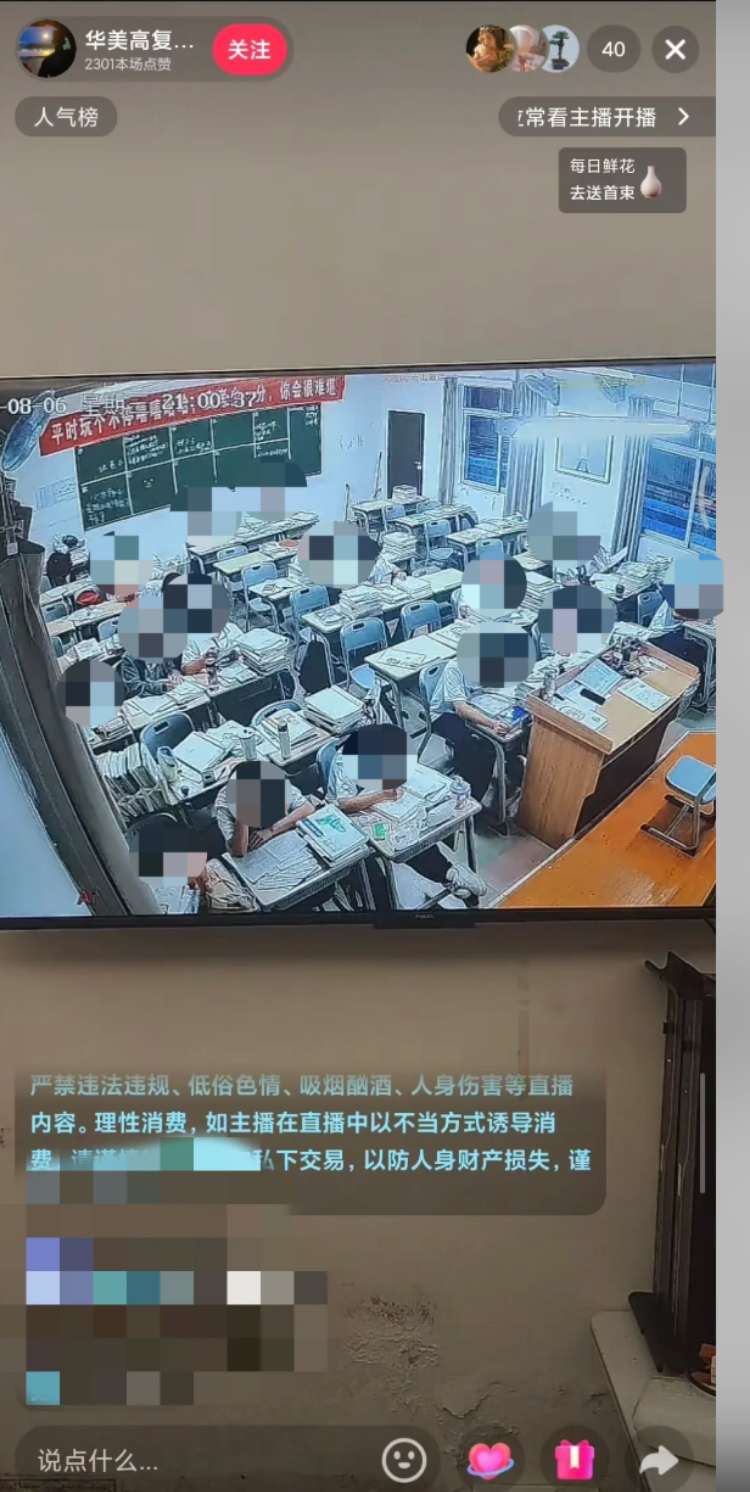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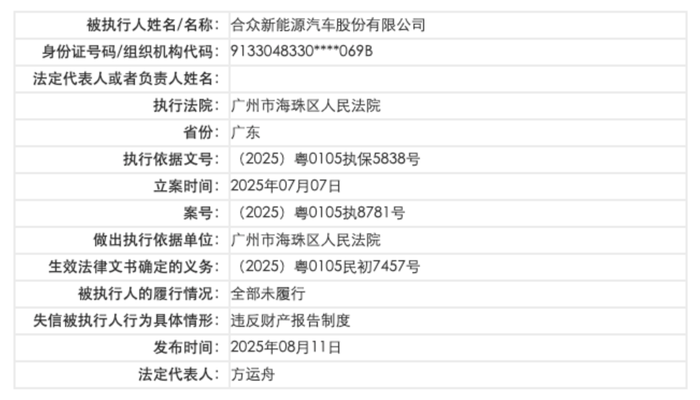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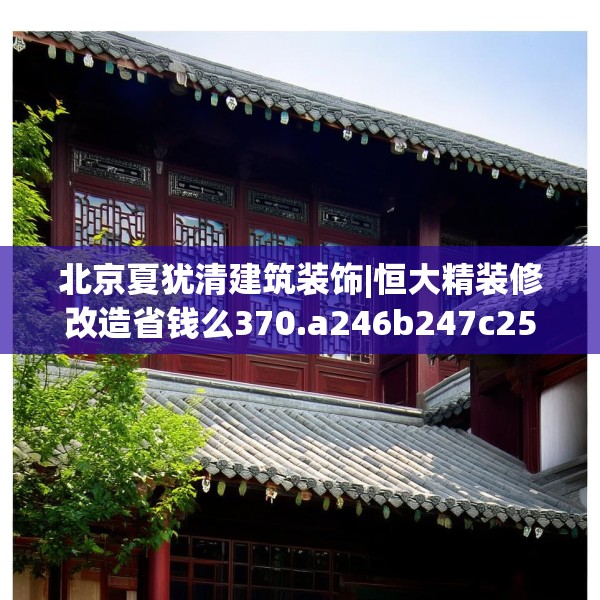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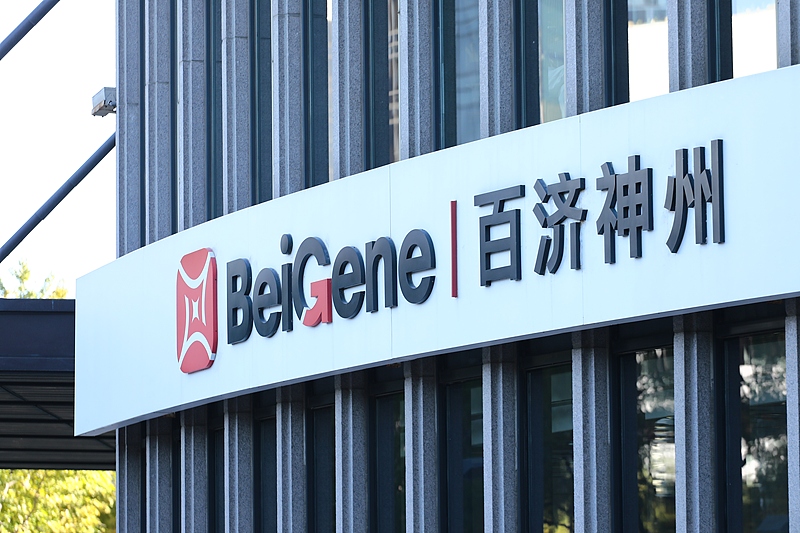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3
京ICP备2025104030号-23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